此文前,诚邀您点击一下“关注”按钮,方便以后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新的文章,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~
文|避寒
编辑|避寒
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她不是黄家小姐,她是个丫鬟,婚书上签的是假名,陶澍知道,没揭穿。
黄家悔婚,丫鬟替嫁
1798年,湖南安化,陶澍十七岁,中秀才。
家境寒苦,父亲陶必铨,教私塾为生,屡试不中,住的是茅草屋,墙上钉书架,桌脚用砖垫高。三口之家,饭桌上常年只有腌菜豆腐。
那年春,黄家派人上门提亲,黄老爷开门见山,说陶澍寒门出才子,家风正,品性好,愿以爱女黄德芬相许。
陶家没谈彩礼,也没推辞,陶必铨只说:“承蒙看得起。”便应了。
联姻定得快,是因为黄家赌了一把。
黄德芬十四岁,刚从女学回家,识字,会作诗,琴棋书画样样精通,但黄老爷知道,读书不值钱,嫁人要看未来,陶澍才气过人,若三年中举,是官夫人;不中,便断亲。
定亲之后,黄家按例给了礼金,陶家不敢动,全数封存。
几个月后,陶澍落榜。
首场乡试名落孙山,榜发布的那天,陶必铨独自走了十里地,把名字从村口张榜的红纸上一笔划掉,他没说话,只回家继续备课。
消息传到黄家,气氛变了,婚礼原定年末,被黄夫人一句“改日再议”拖了过去,之后几个月,黄家不再主动联系陶家。
变数来自盐商吴家。
吴家富甲一方,吴公子带着厚礼登门,开口就说:“愿娶黄小姐。”黄老爷算账,陶澍一介寒生,无官无职;吴公子银两过万,开口便是十间铺面陪嫁。
黄家要毁亲,得找理由,黄夫人说:“陶家太穷,配不上。”
这时,黄家的一个丫鬟站了出来,春兰,十六岁,自幼服侍黄德芬,识字,会做针线,安静寡言。
她跪在厅前,说:“老爷若不愿让小姐出嫁,我愿代替小姐成婚,以义女身份。”
这句话救了黄家的面子,黄老爷当即决定,调包。
春兰改名“黄德芬”,登记入族谱,原小姐则以“外出亲戚家养病”为由,暂避风头,全家知情者不过五人,事后各得封口银十两。
陶家收到消息,婚期订在腊月初五,黄家未派迎亲队伍,只送来两名仆妇、一辆旧轿子、一封简书。
婚礼简单,陶家人看着“黄小姐”脚未缠,手有茧,陶必铨问:“黄家小姐怎如此打扮?”春兰低头不语。
陶澍什么都没问,他只说:“我娶的是德芬。”
婚后,春兰每天五更起床,扫地、汲水、做饭、洗衣,晚上守灯陪陶澍读书,偶尔替他磨墨抄书。
她不会吟诗,也不弹琴,唯一做得好的,是把屋子打理得干净整洁。
冬天,陶澍手上长冻疮,她做了姜水泡他双手,油贵,她用自己做饭的油煎药。
陶澍不问她出身,也不问黄家的事。
春兰心里明白,这婚姻,是她主动争来的,她从没奢望陶澍会爱她。
寒门夫妻,共渡困局
结婚第三年,陶澍再次落榜。
当年是1801年,安化连年歉收,米价飞涨,陶家书塾停课,欠租三个月,地主登门催债,陶必铨将书本变卖,依旧凑不足。
春兰把唯一一件绣花手帕拿出来,说:“拿去当了,能顶几日。”
她不是客气,是真的只有这一样值钱,陶澍沉默,把帕收进袖中,去了集市。
回来后,他把换来的米煮了粥,俩人吃了一锅,屋里暖了一夜。
第二年春,陶澍再赴京赶考,路费由春兰缝制手工衣物卖得,她做了六双鞋,四件冬衣,全卖掉才凑够银两十两。
临行前,她只说了一句:“小心路上。”
陶澍那年二十二,进京考试,历时三月,初试、复试、殿试,层层递进,三月十八日,放榜。
陶澍高中进士第二甲,钦点翰林院编修。
回家报喜,百里皆知,安化书院贴出红榜,称陶澍为“本邑第一人”。
嘉庆帝召见新人,陶澍进宫时,衣领发黄,礼服租来的,他低头答对,话不过十句,却被内阁总管记下:“神色沉稳,文理通透。”
朝廷任命很快到,需填家庭籍贯与配偶信息,陶澍回家后,拿出文书,问春兰:“你真是黄家小姐?”
春兰沉默良久,说:“我是春兰,原是丫鬟。”
陶澍看了她一眼,那夜风大,屋门咯吱响,他没说话,只把春兰的名字填在文书上:“配偶黄德芬,女,黄氏义女。”
没有揭穿,没有更正,此后,她再也没提过“春兰”这个名字。
陶澍赴任北京,春兰随行,衣不华,语不多,她坐在车里,手上抱着一卷旧布,是做鞋底的。
两江总督,一品夫人
1805年,陶澍赴京任翰林院编修。
初到翰林院,住在西长安街小巷一间偏屋,屋漏,地湿,夜里要烧炭驱寒,春兰在屋里生火煮饭,用旧布遮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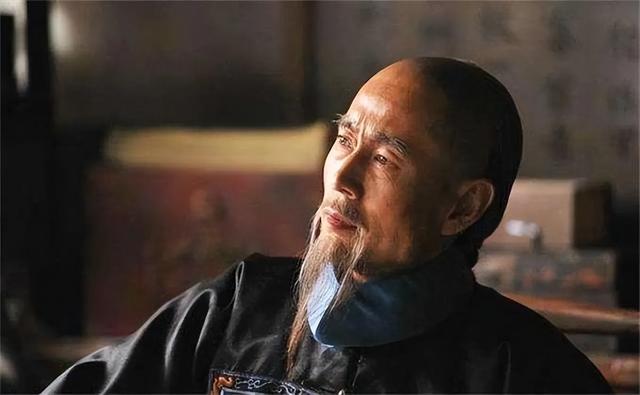
翰林院事务繁杂,多是誊写、抄录、校对,陶澍不言苦,日夜伏案,闲时抄录《资治通鉴》十卷为自习功课。
嘉庆年间,贪风渐起,清廉官员难得,陶澍被记住,是因为敢说话。
18009年,翰林院编修陶澍上疏,反对“捐纳进阶”制度,朝中诸臣皆回避,他独自一人递折,言辞犀利,嘉庆帝批:“尚书房存档。”
从翰林开始,陶澍一路升迁,两年后任户部主事,后调湖广总督衙门为幕僚,主办漕运案。
1814年,陶澍升江南道监察御史,负责司法清查,重审“黄河案”、“银票案”两宗积年旧案,处理得当,无一冤情,朝廷嘉赏。
此后十年,陶澍履历几无瑕疵,政绩突出,节俭自持,从不宴客、不收礼。
1830年,道光帝召见,任命陶澍为两江总督,加太子少保衔。
这年,陶澍五十一岁,出任江南最高长官,辖江苏、江西、安徽,治水、理赋、整饷、剿匪,政令繁多。
陶澍到任第三天,废除运河税卡三十六处,仅此一项,每年节银一百六十万两。
之后整顿漕运,实行“官运民漕”制;开南京铁铸厂;查贪官七十六人,罢免者三十二人。
江南百姓送匾:”不避权贵,敢言直行。”
陶澍不建私祠,不受匾额,回信说:“为民立事,不必留名。”
这一年,春兰被册封为“一品诰命夫人”,敕命由礼部送至南京督署,春兰接旨当天,衣服还是她亲手缝的粗布褙子,未改习惯,未添首饰。
陶澍让人传话:“她不出堂,不接贺客。”
三品以下夫人皆来求见,被婉拒,督署仆从私下议论:“这位夫人,听说是义女出身,旧日是丫鬟。”
陶澍听闻,只说:“她是黄家女。”
多年后,左宗棠被引荐入仕,曾记下陶澍一言:“娶妻,不问身世,只看人品。”
春兰执掌内务,不干政,不出门,府中上下百余人,从未有人见她发火,晚年,春兰仍每日早起,亲自打点家事,陶澍夜归,她亲手温酒,偶尔重病,也不肯让婢女照料。
陶澍命人重修祖坟,将春兰父母并列于旁,立碑:“配黄氏。”
真小姐的结局
黄家小姐,嫁的是吴家二公子。
吴家原本做盐起家,经营晋商路线,富可敌县,黄德芬嫁入时,三金九银,十六抬轿,轰动一时。

婚后不久,吴家因私运私盐被查,吴公子涉案,逃亡途中,被押回长沙,死于牢中,黄德芬成寡妇,二十岁,守寡带子,家产被族人侵吞。
她搬出大宅,靠变卖首饰度日,,住的是小巷破屋,冬天窗口漏风,夏天积水成塘,她没回过黄家,也不再写信,娘家已将她视为“弃子”,无人探望。
陶澍回乡时,曾送人登门问候。
随行官员带来银五十两,说是“旧识赠礼”,黄德芬不收,她听说春兰如今是一品诰命,默然许久。
她说:“我不配收。”那晚,银子被盗,第二天清早,邻人发现她投井自尽。
陶澍听闻,无言,只让人在县志中留一句:“故人之女,不幸而终。”
春兰得知后,烧纸一晚,她没有说话,只在灯下坐了一夜。
历史之外的故事
陶澍病逝于道光十九年,享年六十二岁,葬于长沙南门外陶家山,春兰为其守孝三年,未再着华服。
清史稿有传,称其“廉明谨正、恪守家风”,未提春兰名。
族谱中,她名正言顺,身份一栏写的是:“黄氏,配陶公。”
当年调包之事,陶家从未公开,知道内情者,早已过世,后来子孙说起,只说:
“祖母出身寒微,但德行无缺。”
友情提示
本站部分转载文章,皆来自互联网,仅供参考及分享,并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;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如涉及作品内容、版权和其他问题,请与本网联系,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!
联系邮箱:1042463605@qq.com